日常生活中,我们体验着喜怒哀乐等多种情绪变化,通常人们将其归因为心理变化。事实上,我们的情绪变化还与生理因素密切相关,因为人体内某些化学物质的变化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研究发现,人的大脑会分泌多种能让人感到快乐、安全和成就感的物质,这些物质统称为“快乐激素”,其中最知名的当属多巴胺(dopamine),它是大脑中含量最丰富的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能帮助传递兴奋及快乐的信息,同时还参与调节多种生理功能。[1]

代表性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
多巴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
多巴胺传递快乐的机制
多巴胺最早由George Barger和James Ewens等人于1910年在英国伦敦惠康实验室合成,1957年Katharine Montagu首先在人的大脑中鉴定出多巴胺。而它被命名为多巴胺,则因为它的生物合成前体是3,4-二羟基苯丙氨酸(L-多巴)。随后,瑞典科学家阿尔维德•卡尔森(Arvid Carlsson)等人在1958年最早认识到多巴胺具有神经递质的功能,并且多巴胺还是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前体,凭借对多巴胺以及该物质在帕金森病中的作用研究,他被授予2000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

阿尔维德•卡尔森及他对多巴胺的研究
前文已经提到,多巴胺是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大脑中的多巴胺经过突触将信号传送到其它神经细胞,其中有一条涉及“奖赏系统(reward system)”的路径被认为与多巴胺传递快乐信息密切相关。所谓奖赏系统,实际是一组神经结构,旨在维护动机显著性(动机、需求、喜好等)、联想学习和正面情感(尤其是以愉悦感为核心的情感)。
换言之,动物和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奖赏机制来加强和激励对机体有益的行为,以利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当大脑发现获得奖励的机会时,它就会释放出多巴胺,大量的多巴胺并不能直接产生快乐感,它更像是一种激励,让我们发现如何才能得到快乐,而且愿意为了获得这种感觉付出努力。简言之,多巴胺的效用是期待奖赏,而不是获得奖赏。[3] (作者注:多巴胺的作用机制涉及复杂的神经学及心理学知识,此处仅作简要介绍,深入理解请参阅相关文献资料。)

大脑中的主要多巴胺路径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多巴胺的生物合成及降解
目前来看,多巴胺可能是最简单的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其化学结构虽然简单,但在整个儿茶酚胺家族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还是合成另外两种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前体。生物体内多巴胺的合成是以L-酪氨酸为起始原料,在多种复杂的生物酶共同作用下完成,首先经酪氨酸氧化酶氧化为L-多巴,随后在多巴脱羧酶作用下脱去CO2即可生成多巴胺。多巴胺也可以进一步被氧化生成去甲肾上腺素,最后只需发生酶促的甲基化过程即能得到另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肾上腺素。[4]
多巴胺的降解过程主要有两条不同的路径,其中所涉及的降解酶是相同的,最终的代谢产物也都是高香草酸,两条路径只是中间产物有所差异。具体说来,多巴胺可以首先氧化生成3,4-二羟苯甲酸然后选择性甲基化得到高香草酸,也可以先进行甲基化转化成3-甲氧基酪氨再将氨基氧化生成羧基同样得到高香草酸代谢终产物。[5]

多巴胺的生物合成及降解路径
多巴胺的“双面”效应
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感觉,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基于多巴胺的这一功能,它在医学上被用来治疗抑郁症。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帕金森病也与多巴胺分泌不足,因此可以利用其代谢前体L-多巴进行治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多巴胺的分泌也并非越多越好,过多的多巴胺分泌甚至会造成疾病,例如亨丁顿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HD)患者的四肢和躯干会如舞蹈般不由自主地抽动,造成日常行动不便。
另一方面,多巴胺也与成瘾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吸烟和吸毒都可以增加多巴胺的分泌,使上瘾者感到开心及兴奋。以吸烟为例,香烟中的尼古丁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从而为吸烟者带来特定的欣喜之感,从吸食的第一根烟开始尼古丁就“绑架”了吸烟者的神经系统,内在的奖赏系统会潜意识地释放积极信号促使更多的尼古丁摄入,甚至给吸烟者带来“吸烟有益”的错觉。尼古丁在体内的半衰期为2-3小时,如果成瘾者停止吸烟,体内尼古丁浓度会迅速降低,就无法继续体验“愉悦”感,并出现戒断症状。事实上,在成瘾之后,尼古丁带来的愉悦感非常有限,吸烟者实际上只是为了避免戒断症状引起的不适才继续吸烟。[6]
结束语
多巴胺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神经递质,主要参与运动、情感和神经内分泌的调节,因此多巴胺系统是近数十年来神经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生物学、医学、神经学等多学科的迅猛发展,目前人们对多巴胺的合成、受体种类以及作用机制有了更深入了解,这些研究成果有望更大程度上将多巴胺用于药物等造福人类,而其所带来的诸如成瘾性等负面效应我们也需要慎之又慎并做到合理规避。
参考资料
[1] 李伟. 多巴胺及其受体的研究现状[J].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 2011, 11(01): 104-106.
[2] Benes, Francine M. “Carlsson and the discovery of dopamine.” Trends in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2001, 1(22): 46-47. DOI: 10.1016/S0165-6147(00)01607-2
[3] 崔彩莲, 韩济生. 天然奖赏与药物奖赏[J]. 生理科学进展, 2005(02): 103-108.
[4] Musacchio J M (2013). “Chapter 1: Enzymes involved in the biosynthesis and degradation of catecholamines”. In Iverson L (ed.). Biochemistry of Biogenic Amines. Springer. pp. 1-35. ISBN 978-1-4684-3171-1.
[5] Eisenhofer, Graeme, Irwin J. Kopin, and David S. Goldstein. “Catecholamine metabolism: a contemporary 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physiology and medicine.” Pharmacological Reviews, 2004, 56(3): 331-349. DOI: 10.1124/pr.56.3.1
[6] 张栋梁等. 多巴胺系统与药物成瘾的关系[J]. 神经解剖学杂志, 2010 (5): 564-568.
关键词:多巴胺 3,4-二羟基苯丙氨酸 L-酪氨酸
分享至: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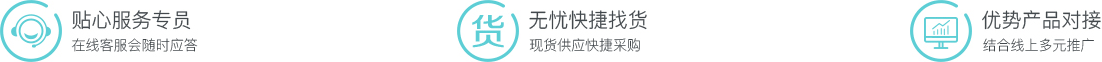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 42011102004299号
© 2014-2025 前衍化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20009754号-1